澳门赌场昆明植物研究所(下简称“昆植”)迎来建所70周年华诞,俗话说“人生70古来稀”,这是标致走向成熟,真是应该好好庆贺一下。“所庆办”等部门发出通知,号召广大职工为所庆写些自己亲身的经历,具体组稿的同志也找到我,希望我写点感受,究竟我也算得上是老职工了,尽管我是“半道”来的,在“昆植”的时间不下40年,如此感情,考虑再三,我与“昆植”似乎还是有点情缘可写的,这才硬着头皮答应了。
事情竟是如此凑巧,“昆植”所庆的日子,恰恰是我与老伴结婚55周年的结婚日,而我又整整大所龄10岁,况且在我们保留了半个多世纪的结婚证书上的介绍人、县长、登记人一栏竟是李玉和——现代京剧红灯记中人物,真是太有意思了。虽说我到“昆植”安家是1965年底,而与“昆植”的接触早在1955年就有了。那是我跟随吴征镒先生从北京到云南来参加“中苏综合考察”,当时的“昆植”是澳门赌场植物研究所的一个下属单位——昆明工作站,蔡希陶先生是站长,我与“昆植”之间还有一点“亲缘关系”,从此来来往往竟与“昆植”结下了不懈之缘,“昆植”抚育我成长,我伴随着“昆植”历经了40多年的风风雨雨。
早年我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北京的澳门赌场植物研究所,到了1955年下半年随吴老来云南。当时的路途没有现在这样方便,从北京到昆明一路上由火车换汽车,又由汽车换米轨的小火车颠颠簸簸到昆明,来回辗转十来天。那时武汉长江大桥尚未建成,我们是随着火车车箱坐轮船渡过长江的,火车到了广西境的麻尾又换乘汽车到贵阳,贵阳再乘汽车经过险境72道拐到沾益,再换米轨小火车颠到昆明,一路转换车旅之苦不说,一路上的客栈的臭虫、虱子更是令人招架不住,好在正是青年也就这么过去了。
到了昆明我被分派到冯国楣先生的采集队里,到西双版纳一带作面上的标本采集,而吴老则陪着苏联专家们到各地作点上的工作,以达到点、面结合的效果。我们的这个“活”,也不比上述一路上的艰辛好多少,在业务上更是一窍不通的我,尽管在学校里到过野外实习,搞过林垦调查,那是学生的事,最多也就是拿到了一块敲门砖,我是学林业的,尽管也学过树木分类学,而且有幸得到国内、外知名的老一辈植物学家陈焕镛等老先生的教诲,到了西双版纳的这个野外现场,简直就是两眼一摸黑,几乎什么标本也看不见,就是有花有果的标本就在跟前,仍旧还是看不见,多亏冯老现场的耐心传授,才免强掌握一些采集标本和认识植物的要领和经验。野外生活也是相当辛苦的,吃的是咸菜和一点燻肉或腊肉下饭,偶尔杀一只鸡,就太兴奋了,真是人间美味;住的是自己动手搭的临时窝棚,床是用树枝排成架高的“弹璜”通铺,每天的工作量很大,尤其是转点的头一、两天,总有70~80号标本,甚至上100多号,而每号标本要采20份,最少也得10余份,再加上头天采回的标本的换纸,这数量可想而知,每当采集归来,吃完了饭就忙着投入标本的整理、登记、挂牌号等紧张的“战斗”,往往都在十一、二点才收工,人是相当累了,随便洗涮一下,一头倒在即坑坑凹凹的“席蒙丝”上,也不感到难受,一觉睡到原鸡(野生的家鸡的祖先)啼,才懒洋洋的起床,吃完早饭又踏上爬山涉水的“征途”。生活总还算是有滋有味,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为了提劲,有时,冯老会惊喜采到了好东西,或者是没见过的,大家也跟着高兴。可是也有最讨厌的,就是旱蚂蟥和马鹿虱子,它们都在人不知鬼不晓的情况下,掉到或爬到人的身上吸血,山蚂蟥吸饱了跑了,留下了直淌血不止的伤口,而马鹿虱子则更恶毒,它吸血是把头埋进肉里,留着身子在外面赖着不走,更讨厌的是它专选人的隐私的部位去吸血,若不小心把它的身子与头拔断,留在肉里的头会化脓溃烂,还引起人发烧,幸运的是这次没有人碰上,也许后来我碰上了。
野外工作结束转入室内进行标本分科及初步鉴定等工作,若能找到较为完整一点的专著就编写初步的检索表,这就由吴老带着我们来做,蔡老、冯老也参加一部分,当时的参考文献十分有限,而我的外文程度极差,中文资料又极少,总是吴老把标本鉴定一个大概,交给我们作进一步的“核实”,有问题再找他,然后编成初步的检索表,刻成蜡板油印出来,如今在我的当年的资料中,还保存着当时吴老的检索表手稿,今天算来也有半个世纪了。
这样室内、室外相结合的传、帮、带,使我在认识植物、读文献、查文献鉴定标本方面提高很快,有了较为扎实的基本功,在科研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至后来1958年再随吴老到云南来,我已能带上小分队,参加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志》、《中国植物志》及进行研究工作,都起到极大的作用。
两次出差云南的时间都在半年以上,1958年则达10个月还多,也没有野外生活补助。在与吴老一起进行野外考察期间,有一件小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物资匮乏,经济拮据,我曾向吴老借过5元钱以解生活之急。吴老慷慨解囊,及时帮我解决了急需。吴老带年轻人的特点是身体力行,常把任务交给你,你独自去完成,有问题找他,最后他会很好的修改你的报告和论文,而我则凡是有吴老参与的纵使是由我完成的工作,署名时一定是吴老在前,比如唇形科某属、茄科某属的研究等等,新等级虽然是由我提出,但命名人一定是吴老和我,因为吴老是我的老师,绝不是拉大旗作虎皮,是一种应有的尊敬,要是我独自完成的,我不敢妄加吴老的名字,怕出了差错连累吴老。记得在1958年初有一天吴老来找我,让我为《科学大众》这一科普刊物写一篇有关西双版纳的稿子,这是该刊物找他的,他让我写,我糊乱的写了一篇题为“西双版纳——生物宝库”的科普文章,结果登载于该刊物的1958年的5月号里,起到了较大的反响,因为当时在北京很少有人知道云南,他们的印象是南蛮荒芜之地,充军、流放的地方,更何况是西双版纳,听也没听过这样的名字。由此,吴老又一次把我带入了科普创作的行列,至今还有一些得益于我科普作品的人,反馈给我他们得益的信息。2004年我与涂铁要同志到保山,到林业局联系工作时,该局长得知是我时,特别派人、派车与我们同行,费用全免,就是因为得益于我的科普作品;也有一些大、中学校的老师也常对我提起他们获益的感受。出版社曾经考虑再版,最终由于版权问题未能如愿。
大概是在1959年或1960年左右,吴老调到“昆植”,按说我应该一起来,可是当时植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行政副所长姜纪五先生不放我,最后吴老只好带着唐耀志先生、黄成就、周铉、武素功来“昆植”,此时,我与“昆植”没有了联系。到了1965年“文革”前夕,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部署,“三线搬迁”,在沿海一带包括北京在内的重要企业、大专院校、科研等机构全部西迁,植物研究所也是西迁单位,同时已选址在安宁楸木园,已经建好房子,到时与“昆植”合并,我此时刚好搞完“四清”运动,被作为先遣队与分类室、生理室等一些同志先来昆明,不料没多久于1966年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植物所的搬迁停了下来,最后,这“三线搬迁”作为是刘少奇的“黑三线”,植物研究所没有搬来,我们被留了下来,从此,我与“昆植”结下了不解情结。其中尽管有些波折,最终还是被留了下来,直至1990年11月退休,在“昆植”渡过了我重要的、多彩的科研人生。
在“昆植”的这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可以说是精力充沛、干劲实足,事业上多少露点头角,从少壮步入中老年的时段,甚至到今天步入老年的时段。尽管一到“昆植”不久就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但在“文革”初期和后期还是干了一些大事,其中如代号为“523”的由军队系统组织的全国南方三省的抗疟药物调查,由我带队并有有关军队、地方等医务人员、药物研究人员等参加的考察队,跑遍了我省的南部地区,其中尤其是西双版纳、临沧和德宏等地区,最后汇总编辑了全部是彩图的《云南中草药》上、下两册,带动了各地州及一些省份编写中草药手册等书籍,从而掀起了全国大搞中草药运动。1973年出版了《全国中草药汇编》上、下两部,以及又编了附卷“彩色图谱”,这为“昆植”无论在地方或全国多少也得到一点声誉,何况云南还是被世人誉称为“植物王国”。
“文革”后期在“抓革命,促生产”当中,虽然植物分类学及学术权威,受到了一些过激的批判,人们一时不知做些什么好,当时吴老尚未解放,尽管他在“牛棚”里的逆境情况下,还汇总各地中草药册子,在被批斗,写检查之余,偷出时间加以全部整理,如此中国共产党党员本色,真令人敬重,是我们后生的楷模。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有些事似乎很自然地落在我的身上。因为当时除了吴老之外,我在分类室的人员当中,除了黄蜀琼、尹文清、周铉外,我的年龄最长,经历一些野外考察、室内编书等也较多,学历也早一些,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各方面都能瞎“嚓吧”(昆明话大概意思是什么事都可以掺和),因此,在“文革”后期带领大家编写了《云南经济植物》,而当时室负责人是方瑞征,她配合着我,工作十分顺利。后来又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革委会”的负责人之一许学勇,又找到我询问我们还可以干什么?此时,我大胆的提出搞《云南植物志》,为什么用大胆这个词,因为在“文革”期间,“植物志”被批得几乎是体无完肤,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的封、资、修产物”,又是在洋人屁股后面,纸堆里讨生活的东西,谁也不想提及,怕的是再挨批。不过我说出了理由,结果经“革委会”及室领导研究后,同意了我的建议并由我带着占分类室几乎3/4的人员齐上阵。此事现在看起来,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说云南的植物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多,就是单想我们的这支编写队伍,在专业方面有搞生态地植物学的、植物地理的、植物生理的、标本室的管理和采集人员等,从文化程度来说,有小学、初中程度的,有大学刚毕业不久的,还没碰过拉丁文、英文程度不高,甚至是仅学过俄语的等等,就是搞过植物分类的也是屈指可数,真是“十几个人来,四、五条枪”,有的人甚至是“植物志”是怎么样的书都不太了解。因为当时这类的书籍确实太少,一般鉴定标本通常是对标本室定好名的标本,可查的文献很少,因此,编写《云南植物志》的难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正好此时吴老已初获“解放”在计划处,我自然名正言顺的去请教他了,将总体设计与一些具体细则都请他过目。在《云南植物志》中最不好办的是在《中国植物志》被批判的重点,是对拉丁文种名的来龙去脉的引证,这对于不是从事分类学的人,甚至是工、农、兵,一般是不会追究它的,或者是看不懂的,但是作为从事植物分类的人或研究的人,则是十分重要的,怎么办?吴老提出了省去文献名称而仅列作者及发表年代的形式,这样使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去追究时有点线索,有个方向通过进一步找有关文献目录等书籍,找到该作者发表论著的具体文献,又可以减少些文字,减轻一般读者因过多地,认为没有必要的东西,加重了书的文字负担。另外,在中文名方面尽量搜集各地的名称(一般称为土名),列入异名中和尽量列举用途,并增加经济植物索引,以便一般人查中文名就可以找到要找的植物名称,以及其用途。这是一个创新,与以往出版的有限的植物志有所不同,这样的做法只是在那种年代的产物,若在今天看起来只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因为直接写出来,让读者查找更方便得多。无论怎么样,像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萝卜头,带着那样的“人马”,搞起了《云南植物志》这部巨著的前期工作,并在某些方面如政局不太稳定,又逢机构改革、经费不足等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完成到第7卷(其中第3卷由李锡文同志承担),我已经是够满足的了。
另外,更使我高兴的是“文革”后,打倒了“四人帮”,我协助吴老带了“昆植”,也是全国植物研究单位的第一位西德留学生——Gaby Lock,1988年她再次来昆明探望我们时,还赠送我一幅她亲手绣的十字绣,很不简单,后来,又与吴老带了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并很高兴我竟然得到被邀请出国的机会,如今看起来出国不怎么稀奇,可是当年出国不但是一种奢望,而且作为出身不好的人是想也不敢想的。最早的一次是1979年左右,被美国马里兰大学邀请去留学,邀请函、申请书等都寄来了,可我没有去成,这不能说不是一点小小的遗憾,因为这毕竟是“文革”后,“昆植”第一个被邀请到国外留学的。可后来“改革开放”了,情况变了,我曾几次被邀请到美国、日本、巴西、厄瓜多尔、加拿大等地,都比较顺利,而且都是对方全程资助。我第一次到美国哈佛大学标本馆时,得到他们的热情款待,并赠我该校的荣誉纪念章和全体人员留言、签名的纪念册,我回国后还来函表扬我在该馆时出色的工作;在密苏里植物园屡次都得到该园园主任、世界著名科学家、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H. Raven的亲切接待;在日本我受到歧阜药科大学全校副教授以上,包括退休的老教授在内的30~40人的最高的礼遇接待,电视台还进行了直播,按日本这个国家来说称得上是较高的接待规格了;在巴西我们这个学术访问团,我是唯一作了学术报告的,第二天在巴西的最大报纸“Noticia”日报报道了我作学术报告的消息,这些都是我带着“昆植”的招牌,似乎是潇洒地走一回。
由于我走上了“科普”的道路,这些年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云南省、昆明市等电视台、广播电台等,都有播放我的科普作品和一些科普活动、作客嘉宾等的情况,直至去年我还不止一次的上了中央电视台。我高兴的是由于“昆植”的名声逐渐高了,我也被捎了进去。就是在退休后的日子里,我拿到的奖牌、奖状、优秀离、退休干部等的证书,似乎还是可能弄出几张的,这是社会给我的认可。
然而,事情总是有两面的,有喜也有忧,有风光,也有无奈。在《云南植物志》编撰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插曲,但无论如何,在所有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云南植物志》顺利出版了。更令人高兴的是,1994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本奖状,原来是《云南植物志》第1~5卷荣获1993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获奖人员竟达9人之多,他们是吴征镒、陈介、李锡文、李恒、闵天禄、方瑞征、庄璇璇、黄素华、徐廷志。这是奖励为《云南植物志》前期出力人员的一个鼓励和有力见证。
世间的事总是如此的凑巧,1999年我已退休,不知是什么原因,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组委会竟几次登门邀请我,到该会主持整个会期的各个园艺作品的比赛工作。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不是学园艺的,更没从事过园艺方面的工作,所以与园艺方面的学者们有交往,这完全是他们看得起我,邀请我参加一些他们的学术活动等等。如今则是硬碰硬,面对的都是国际上的国内、外知名园艺专家、学者,若有差错,丢我个人的面子不说,还有损国家的声誉,那才是大事,可是我再三推辞不掉,最后,我只有拿我还有《云南植物志》豆科的编写任务,并且年底要交稿,所以不能去的法宝。不料,对方则以国家的任务、大局为重等言词对我,并提出要发公函与所方协商,将我的豆科任务向后推延一年,果真他们办了,并将有所领导批示同意的公函给我看,这时我才无奈投入“世博会”的工作,在“世博会”结束时,还特别把对我的工作鉴定书寄给“昆植”(1999年10月31日),对于我在“世博会”期间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同时在1999年11月15日又向“昆植”发了感谢信,声称“……贵所在科研工作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发扬了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精神,把本单位著名专家陈介教授推荐到组委会秘书处协助工作,同时积极主动解决借调人员的科研工作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以具体行动支持博览会的工作。正是由于贵所领导的高度重视,博览会才有今天的成就。”等语,“世博会”结束,我来不及高兴又投入豆科整体的研究和编写我自己具体承担的部分。
虽然在余下的《云南植物志》编写过程中出现了太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以至于我过早的离开编委会,但这段历史可作为前车之鉴,值得后人去思考和总结。令人高兴的是,我虽然退休,但活得还十分惬意,曾蒙各方看得起,一年到头还挺忙,找我评成果、评论文、评职称和审稿的还不少,就是国外的学术刊物,也来找我审稿。最初他们找到我的学生要我的地址,后来,竟找到标本馆同志的信箱(Email),发来稿件由他们转给我,我不得不在所里的平台设了一个信箱,由我的学生代为管理。我想这些老外不认中文,或者不知道有“陈介先生行将退休”的说明,所以这些老外至今还找上门来;或者是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有著作和论文在国外出版发表,他们没在意的原故。
更值得我欣慰的是,我的一帮学子们,个个都比我强,比我有成绩,都是博士生导师、行政领导、院长等,他们带的学生也很出色,而我也仅仅是当年的一位“领导”罢了。他们都较忙,但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的,逢年过节不是打电话就是寄贺卡,在昆明的无论白天多忙,就是到了晚上10点以后,也还要带着孩子回家来探望祝贺。有一次有位学生在“教师节”来探望我时,谈起他招学生时,他要求学生的是,先要学会做人,我非常赞扬他的作法,竟想不到他回答我说:“陈老师,这是您当年教我们的”,顿时我十分快慰,为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这才是“昆植”从吴老、蔡老、冯老等老一辈科学家传承下来的人间正道。
如今虽已超古稀之年,却又参与以吴老为首的国家项目——《中华大典》植物分典的编纂工作,事情竟又是如此的巧合,我又被出版社抓来作前期工作,“植物分典”的编写总体纲目框架,竟又是由我先拟出初稿供大家讨论完善定案的,我这架老牛破车至今仍在拉着。回故往事,“昆植”给我的真是太多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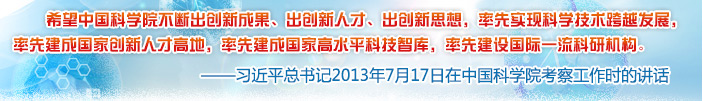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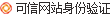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