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的时候,转学到茨坝镇的中学开始初中生涯。那时的茨坝还是一个夹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和农村之间的小镇,我的母校就在这个小镇的边缘。据说穿过三十四中东边的玉米地和果园有一个鸟语花香、彩蝶飞舞的“百草园”。
“百草园”在我脑海中想象的似乎就是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描述的情景: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形态奇怪的何首乌。虽然鲁迅先生百草园中关于美女蛇的传说已经不攻自破,他提到的赤练蛇依然是我们时常遇到的金环蛇的形象,对“百草园”感觉在神秘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惧怕。年幼的好奇心屡次引诱我们对神秘的“百草园”一探究竟,而植物园高大的墙壁让我们望而兴叹。不知什么时候,高墙上多了几个人工凿出的小坑,我们通往这个神秘之园的大门逐渐打开。
穿过墙边一片密密匝匝的杉木林,虽然我们没有找到皂荚树和桑椹,也不认识何首乌的样子,我们却在裸子植物区的大草坪找到了我们的乐园。草坪上零星点缀的松柏灌丛好像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是捉迷藏最好的藏身之所。青草的味道随着我们的每一个脚印、每一次翻滚沁入鼻腔。因为是偷偷爬墙进来,每每看见有人就十分胆怯,立刻遁到茂密的草丛中。也不敢跑到有房子的地方,那时与扶荔宫失之交臂,可能就是这个缘由吧。墙上的小坑和我们一起渐渐长大,直到有一天被填上了一层厚厚的水泥,通往这个乐园的道路又被阻断,我也转入市区开始了高中三年。
那时,疑惑园子的名字为何名曰“百草园”,只听爷爷说园子里面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高中和大学的生活大多在市区度过,童年的乐园再也没有造访,茶花园倒是每年春节全家踏青的必游之处。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切似乎都与昆明植物所毫无牵连。
年幼时的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和对未来的抉择。或许是“百草园”的缘故,亦或许是大学教植物学的先生极具吸引力,催化了我对植物分类学的浓厚兴趣并要为之而探索。大学时代即将结束前,我有幸进入昆明植物所开展本科毕业论文,师从王红研究员和顾志健研究员,开展了有关植物染色体的工作。那时,不但要学习从细小的根尖中寻找染色体的技巧,还要学习如何冲洗胶卷、放大照片。如今,暗室已经被数码照片取代,然而在显微镜下认真仔细的寻找染色体仍在继续,探索未知世界的科研仍在继续。在实验室的旁边有一个园子,因其中植满了各种稀奇的中草药,故名:“百草园”,哦!终于为儿时的疑惑找到了答案。
本科结束后考入了昆明植物所继续硕士的学习,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接触植物和大自然。喜欢雨后云雾缭绕的高山,江水滔滔的长江消失在群山之中;惊叹高山流石滩植物夹缝中求生存的顽强和不屈;对植物及其传粉者的协同性更是不解,没有造物主的精心安排,这样的巧合怎能存在?植物所的学习和生活并非时时如此诗意,忘不了实验室里通宵达旦的热闹景象,感激导师对文章论文的句句斟酌、字字推敲,更难得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学友,交流间互补专业上的不足。一番激烈的争论虽免不了些面红耳赤,但几杯啤酒催化下,又继续战他几十个回合。学术上老观点的重新认识、新观点的产生,本源于此。钦佩那些耄耋之年还继续活跃在科研岗位的老先生们,他们体现的是一种对事业的执着和追求,更是一种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方式。
第一次听英文的学术报告还是在标本馆老楼二楼,那次吴征镒院士还亲自到场,之后由于身体的缘故,以及忙于将其几十年之大成著书传世,在学术报告厅能见到吴老的次数越来越少。标本馆老楼的墙上原来郁郁葱葱的爬满了葛藤、爬山虎和何首乌。几年之后,这一抹翠绿被从根剪断,岁月的痕迹也被覆盖于白色的瓷砖下面,唯独窗外的桉树依然屹立在风中,哗哗作响。
儿时记忆中的“百草园”已成为心中神圣的科研殿堂,一个探索和诠释植物世界神奇现象的大课堂,自然界是老师,我们是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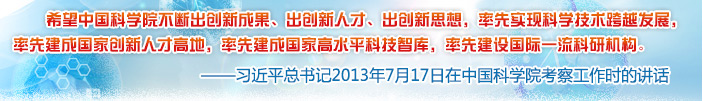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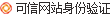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