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6月18日我踏进澳门赌场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大门起,至今已有30年了。可以说,我的科研生涯基本上是以植物所为背景、在植物所逐步发展壮大的历程中渡过的。在昆明植物所建所70周年之际,回忆往日的岁月,仍令人难以忘怀,而其中在自己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自己30年的成长岁月一直与“二萜生物碱”相伴,实在是一种“缘分”。
30年前,我是作为贵州大学教师派遣到昆明植物所进修植物化学的。刚到植物化学研究室时,正值周俊老师带领杨崇仁老师、杨雁宾老师、浦湘渝、陈昌祥等开展云南著名传统药物的化学成分研究,我在杨崇仁老师指导下进行黄草乌中二萜生物碱的分离与结构鉴定。当时陈泗英老师已发表了我国第一个新结构二萜生物碱—“滇乌碱”的结构,可以说是昆明植物所该研究方向的开始。30年前昆明植物所的科研条件在国内可以说是很好的,尽管当时的黑龙潭因地处偏僻被人戏称为“夹皮沟”,但昆明植物所已经有了90兆傅立叶变换核磁共振仪,有足够的图书资料供查阅,加上实验室整日充满了朴实、紧张、和谐、团结的氛围,实在是一个理想的科研场所。在周俊老师、杨崇仁老师、王德祖老师、陈泗英老师和实验室其他老师的帮助下,自己的进步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周老师指导和鼓励下完成了黄草乌中二萜生物碱的分离鉴定;参与开展了利用核磁共振碳谱技术测定乌头碱型生物碱的研究;完成了乌头属植物二萜生物碱综述的化学部分;并在《化学学报》和《云南植物研究》参与发表了4篇论文,没有想到的是,从此我与二萜生物碱“结缘”。
1982年考入了昆明植物所作为周俊老师的硕士研究生。1982-1984年间在兰州大学完成课程学习阶段,曾协助吴凤鄂老师的博士研究实验工作,内容也是二萜生物碱。1984年回所进行研究生论文研究课题,在陈泗英老师和周俊老师指导下,仍然继续国产乌头属和翠雀属植物中二萜生物碱的研究。此间受到周俊和杨崇仁老师学术思想的影响,开始对国产乌头属植物的化学分类产生极大兴趣,在几位老师指导下完成了“国产乌头属植物的化学分类”并在《植物分类学报》发表。其中有关化学结构与该属植物系统之间相关性的“玄机图”还是女儿出生时在贵阳医院里用茶杯盖子当圆规画出来的。该项研究结果尽管有些粗糙,却也在1984年全国第一次植物化学分类学术会议上得到好评。
我的导师周俊对学科发展十分敏锐,颇具远见和前瞻性,使我终生受益。记得在1981年就曾先后建议我转向植物皂苷或植物环肽的研究,尽管后来他对我的发展方向另有部署,但这两个方向都已成为今天我所植物化学研究室的重点研究方向。记得1985年植化室曾举行了植物化学发展研讨会,正值我的硕士生涯完成之际,周老师则苦口婆心地开导我一定要将学习重点放到有机合成领域,并促成了我学术生涯中第二个阶段的学习—到日本京都大学化学研究所富士薰教授实验室从事有机合成研究,为我后来的学术发展和科研特色(植物化学+有机合成)奠定了基础。也许是我性格的“惯性”所致,我仍对二萜生物碱“情有独钟”,就像年轻人热恋中的情人舍不得放弃。在继续文献查阅中发现蔷薇科绣线菊属植物中竟然也含二萜生物碱!而虎皮楠科植物中那些结构怪异的化合物居然也称之为三萜生物碱或二萜生物碱!这种惊奇是基于自己当时的知识面十分有限所致,但却成为想“碰”这些植物的驱动力(Driving force)。得益于冯国楣先生和武素功老师的帮助,在出国前准备了植物提取物样品,并在日本近5年从事天然产物合成的岁月里,成了有机反应实验余暇自由研究的内容。当时我也没想到这种余暇研究的影响会延伸到现在。
粉花绣线菊复合群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除了众多的新二萜生物碱和二萜外—这要感谢大自然的恩赐,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我所顾志建、沈月毛、孙航、澳门赌场动物所的陈全课题组合作,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次,从化学与生物学不同学科,针对该复合群开展了化学成分的结构、特征性反应、合成、仿生合成、生源途径、药理活性、植物染色体、传统分类与植物化学分类、生物地理等方面研究和探讨科学问题和学术观点,使我们加深了当代植物化学研究体系的认识和理解。值得提出的是,正因为悬而未决的乌头属二萜生物碱生源途径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徘徊在我的脑海中,才使我对绣线菊中的二萜结构产生格外的敏感和悟性,从而导致其生源前体二萜化合物的确定以及Double Mannich仿生反应的发现,一直到由二萜生物碱生物合成途径的阐明。
如果说粉花绣线菊复合群中二萜生物碱的研究是必然结果,而虎皮楠属植物中二萜生物碱的发现则带有某种偶然性。记得1985年到西双版纳去采集牛耳枫的种子,是对其中所谓的“三萜生物碱”和“二萜生物碱”成分感兴趣。但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令人失望:因为虎皮楠生物碱初步的生源研究结果表明,其前提应该为角鲨烯,经氧化生成具有戊二醛基本结构单元的衍生物,再与胺类化合物经Double Mannich反应、Diels-Alder反应及进一步的环化反应形成基本骨架,这已经超出了“伪生物碱”(Pseudo alkaloids)的概念范围,严格意义上讲不能作为“三萜生物碱”,更谈不上其碳骨架降解产物为“二萜生物碱”。因此在90年代初期我们在《云南植物研究》发表了初步的研究结果后就停止了虎皮楠生物碱的研究。直到2005年末,文献查阅在《云南植物研究》发表的文章竟然有较高的引用率,这才发现该领域研究已成为热点。鉴于课题组邸迎彤等研究生提出后续研究的建议,经过认真考虑才下决心重新启动。两年多的研究结果已从中发现包括11个新骨架类型的近90个新虎皮楠生物碱成分,但与“二萜生物碱”的概念相差甚远。可是,李春顺等同学的研究中居然在该属植物中先后也发现了系列典型的乌头属植物中的二萜生物碱!重新引起我对二萜生物碱的思考。尽管同学们对这些已知结构的二萜生物碱感到失望,我曾对他们“调侃”说,如果你能从虎皮楠生物碱生源的角度解释这些生物碱的来源,你不妨把这些二萜生物碱当作“新骨架的虎皮楠生物碱”!其实,到底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不知道,但需要进一步付出。
30年了,二萜生物碱总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这种“缘分”实际上牵连着很多其他的“缘分”:我在30年前能有机会到昆明植物所学习是一种重要的缘分,成为周俊老师的学生是影响我一生的缘分,能有众多优秀的学生也是很关键的缘分。我曾经说过:“幸运的是,我当学生的时候有好老师,当老师的时候又有好学生。”离开这些缘分,就不会有与“二萜生物碱”这样的缘分。最后我想说:缘分与你的努力和付出相伴,与你的机遇相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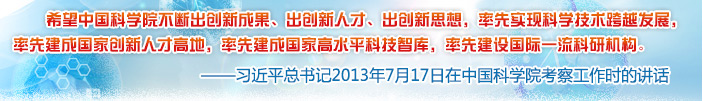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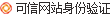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