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雨天,我站在窗前,伸我的手出去,倏地就回到儿时老屋的屋檐根儿下。那时,雨水顺着瓦楞汇聚成小河,砸在水洼里就弹出一只小金钟;我光着脚,把它们都埋在泥里;小燕儿从瓦楞里探出头来,咕噜咕噜;隔着玻璃窗,奶奶的吟唱像梦魇般迷离……
不晓得时光用什么法术,怎么就能让我站在两个点,硬是分不清哪个才是真实的存在。我闭起眼来,小金钟的咕嘟声,老屋的味道,儿童的心思,已成为现在的我的一道风景,那画里的我真的是我?
我捧起一手心的雨,想问问它们是否轮回于十几年前的某个雨天,它们不睬我的踯躅,它们也未并经意过自己的变迁,没有经历变迁,也就无所谓迷失了。
有风,送来一串雨珠,拍在我裸露的手臂上,我的心一惊,是顽童无忌地挑逗呢还是经世者善意地劝慰?反正,游离的幻梦光一般地飞远了,我这才感到了周身的冷。年月从不因谁的节奏而多耽搁一秒,是《卡农》也好,是《月光》也好,是《谐谑曲》也好,反正只演奏一遍,才不管你喜欢回味哪一种风格。
有闪电,狰狞着包围过来,我的懦弱无处躲闪,我的心一紧,是强词夺理地囔嗓我呢?还是挑衅一般地嘲笑我呢?正像我日渐看到的丑陋的人和事,在他们面前善良和软弱没有分别,我蜷缩成一团,我不敢反抗他们,却不甘顺从他们,难道他们也想把我的丑陋唤醒,接着和他们扭打成一团,比比谁更野蛮?我始终没有办法,但越来越倔强了。
有雷声,轰轰隆隆地滚过来,我却变得泰然自若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各种遭遇、污秽,逐渐见怪不怪,也开始嘲弄自己当初的执着信仰了。但,还是不甘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就是不能用“穷则独善其身”抚平那份愤懑。
其实,雨有一种情怀,是敏感。
她令我感伤,因着我们敏感的共鸣。
我走入雨里,不想撑伞,也不愿人们看着我,不是惆怅,是真实,不是体验,是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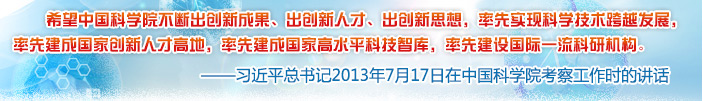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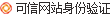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