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疫情暴发后,野生动物与疫病的关系逐渐得到揭露,多少年来屡禁不止的食用野生动物问题开始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一些地方正准备通过立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有害社会的行为,通过法制手段遏止是必要的,然而多年来的实践又告诉我们,对于那种社会牵涉面宽、危害性比较隐蔽的问题,包含着大量的群众性认识问题,在群众的思想认识还处于比较模糊的背景下,单纯的法制手段是很难奏效的。实际上,在讨论立法的地区,一些深层次的认识问题已经浮出水面,而且还很有代表性,如果这些认识得不到澄清,立法本身都很难成功,更遑论执法。
一种意见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从野生生物中寻求食物来源的历史。从野生生物中扩大食物品种以提高人们的膳食水平,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文明进步的表现,因此不能一概禁食。迄今人类所有的食物确实都来自野生生物。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采集狩猎的社会活动,甚至到近现代,有的民族还以采集狩猎为主,那是为了满足基本生理需要而利用简单工具进行的自给性活动。这种采猎活动的环境影响很有限度,但即使如此,也出现了资源枯竭的危机,因而,后来才出现了野生生物的驯化和种植、养殖,从而带来了农牧业的兴起。现有的农牧业产品品种经过数千年的筛选和改良过程,与野生动植物已经有了根本区别,它们的利用无论对人类还是对环境都是相对安全的。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无疑应当继续开展野生生物的驯化利用,为社会造福;然而从社会消费的层面看,对野生动植物,尤其是对陆生野生动物的食用,已经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基本生理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猎奇心理的奢侈性需要,甚至是体现身份的伪假性需要。为满足上述需要而进行的采猎活动是一种谋利性的经营活动,即使穷尽天下飞禽走兽恐怕也难以填平这种欲壑。在工业化迅速扩展的今天,野生生物及其生境正在迅速丧失,人为的商业性采猎只能加快物种的灭绝,同时还有染病之虞。在对待野生生物的问题上,考虑到受保护物种和一般物种的区别,不能一概禁食,但也绝不能一概以文明颂之。对于社会层面来说,这是一个价值导向问题。有的地方已经把“禁食野生动物”的立法原则改为“不滥食野生动物”,但如果社会上仍然把食用野生动物视为一种荣耀,那么,即使立下“不滥食野生动物”的法规,也是很容易被冲破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野生动物的驯化已成为一种新兴产业,如果一概禁止经营,会对经济造成打击,同时也不利于物种保护。驯化利用野生动物确实既能满足人类正当需要、又能保护生物物种,但是其中的情况千差万别。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受国家保护物种的商业性食用、驯化和养殖应当完全禁止,因为短期驯化的野生动物很难与未驯化动物从外观上区别开来,在分布极广的经营场所中,两者极易混淆,这就为非法捕猎留下了可乘之机。实际上对于一般的陆生野生动物不宜提倡食用性商业驯养,因为一般物种的捕猎虽然可能对环境影响不大,但有可能传播疫病。
在我国,食用野生动物的历史源自中医理论的“药膳”之说,这种药用价值在现代商业环境中被推到极端,成为一种炫耀身份的“享受”,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力。只要这种邪恶的欲火不灭,食客们就不会满足于“驯化”而必然追求“天然”,最后使所有的社会努力化为乌有。禁止野生动物的餐饮性经营,从短期看可能会对经济性的驯养带来困难。在此必须指出的是:第一,困难不是绝对的,因为已驯化动物不用于膳食,还可以有他用;第二,禁食野味是大势所趋。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与大自然共存共荣,已被国际社会视为文明与否的一大准则。我们希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在生活习惯上痛切地革除陋习。无论从环境保护、疫病防治,还是从国际交往的角度看,饮食文化的变革都势在必行。实际上,提高膳食水平的更广阔空间是食品的有机化和安全化,在此,养殖业有异常广阔的空间。
有人提出,野生动物中也有危害人类的物种,如果它们能被经济利用,是否有必要禁猎?天然生态系统的形成是各种自然要素自组织的结果,每个物种都有特定的位置、发挥着特定的作用。野生生物的危害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生态关系的正常表现,是一种相对的危害;另一种是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破坏,是一种绝对的危害。对于前者,只能把危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例如肉食动物虽然可能伤害人畜,但如果没有它们的调节,过度繁殖的草食动物就会毁灭植被、传播疫病,从而造成更大的危害。对于后者,如果某一物种反常繁殖,在一定范围内当然可以通过捕猎加以利用,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最重要的是设法恢复生态平衡。一般说来,有经济价值的动物都不是适应性特别强的动物,如果本末倒置,可能会从相反方向加剧生态的失衡,还可能带来错误的价值导向。
病毒在大自然中的存在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实,它们的变异和蔓延就是生态失衡的结果。SARS疫情控制之后,我们应当痛定思痛,应当把考虑问题的基点放在如何保护而不是如何食用方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来一个情感、情趣的改弦更张,那么在未来的岁月中将很难避免新的灾祸。(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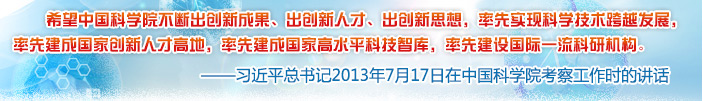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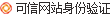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